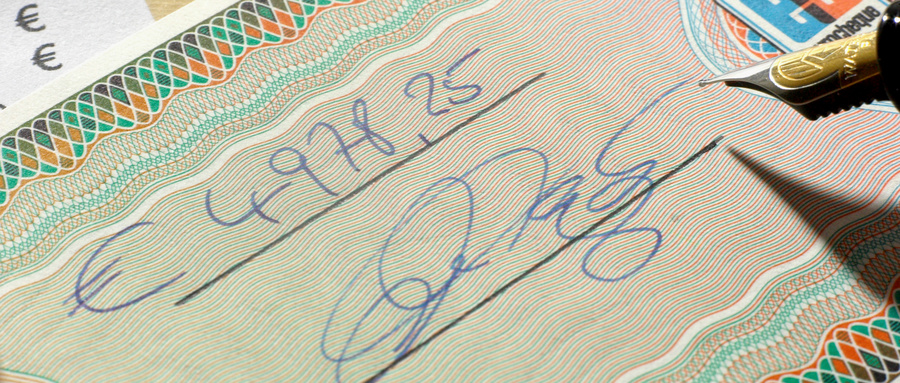“票据法”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市场主体难以获得法律上绝对的豁免权。于是,某类市场主体便采取某种规避法律的手段来开展业务,特别是当不同的监管主体在各自独立的法律系统下采取了区别了监管政策的时候,“严监管”业务模式倾向于往“去监管”或“宽监管”业务模式逃逸,此时便产生了“监管套利”。

所谓“监管套利”,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经济目的可以通过多种交易模式来实现,而对于不同的交易模式,监管主体、监管规则、监管阶段、监管限度等监管要素可能会存在差异,此时便存在着监管套利的空间。
“监管套利”可以分为为五种类型,即:
从一个监管主体转到另一个监管主体
从一个时间段转移到另一个时间段
从一种市场主体身份转为另一种市场主体身份
从一种业务形式转换成另一种业务形式
从一种披露方式转入另一种披露方式
对于票据贴现而言,因为其本质上是一种票据融资行为,除了贴现以外还可以其他社会化的方式来达成,比如票据的资产证券化就是一条“监管套利”的方向。
2016 年全国首单票据收益权资产证券化产品———“华泰资管一江苏银行融元 1 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由此创设了一种票据 ABS 模式。
票据 ABS 模式采用了“收益权转让+票据质押”的业务框架,来规避相关的法律限制。
因为“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限制了票据的非贸易转让,所以票据资产无法直接背书转让来入池,所以便创设出一个“票据收益权”的概念,并以此来作为基础资产即转让标的,使得原始持票人与计划管理人( SPV) 之间形成一种基础资产买卖关系和票据质押关系,以此来实现与票据贴现相一致的融资目的。
但此种 ABS 模式缺陷甚大,不仅“票据收益权”这一生造概念不伦不类,与民法基础体系不相容,且难以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和有效的破产隔离,这又与资产证券化的规则体系相冲突。
所以悬之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仅有“票据法”,还有其他金融监管文件。
比如 2018 年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因为把“票据收益权”排除出了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范畴,这种业务模式也随之一度停滞。
为解决上述问题,2020 年人民银行又发布了《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明确票据在存托时可以背书方式将基础资产权利完整转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票据的非贸易转让,对“票据法”第十条进行了突破。
但此时,“票据法”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又开始发挥作用。
比如宁波银行和华泰证券在其标准化票据的产品设计时,都要求对商业汇票原持票人的贸易背景和交易关系进行严格审核,[6]而且普遍比商业银行贴现业务的审查更为严苛。
可见,这种监管套利实质上是在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将票据贴现从银行业务转向至证券业务,使市场主体、业务形式、披露方式及监管主体都实现了空间挪移。
但之所以效果不佳,归根结底还在于法律豁免权的不确定性,而监管沙箱解决这一问题就更为直接和直观。
监管沙箱的本意就在于提供一个安全可控的空间,这种空间即是业务活动的范围,更是一个对现行法律的相关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享有豁免权的空间。
俟其业务的安全性获得验证,并与立法者共同健全起一套适宜的法治环境,那么作为一种豁免补偿途径的监管套利也就失去了必要性,从而也减轻了相应的监管负担。
但兴业银行的“‘融宝通’中小微企业票据流传支持产品”又明确其“不涉及企业与企业间票据流转业务”,这种固化的边界设定也限定了金融业态,对银行以外的其他市场主体和其他的业务形态很难起到探索和实验的目的。
所以,既然是创设一个实验性“沙箱”,便应以不设限的方式来探索出边界明确的规则来抑制监管套利,如果对监管套利起不到抑制作用,那边意味着不可能减轻监管负担,同时也难以激发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创新。
以上就是关于“由票据贴现说起:监管沙箱与监管套利”的全部内容,相信大家已经有了全面认识;更多票据相关资讯及知识,欢迎关注商票圈票据学院。

免责声明:来源于陈劼。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此文章并不代表本平台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文章有任何不妥之处请留言指正或联系删除。